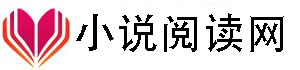40-50(8/56)
。少女的脸颊出现满脸通红时,最大可能往往是碰见自己的心上人,第二可能则是火气上涌导致满脸通红。但稚陵深知觅秀姑娘没有什么看得上眼的男子,那无疑,一定是遇见了令她火冒三丈的事。
她贴心地给觅秀姑娘倒了杯冷茶降降火,觅秀尚未觉察到她的动作,只深恶地皱着眉,喝下一大口冷茶,大约是唇舌得到滋润,随后骂人的话倒豆子一样倒出来:“奶奶的,……”
稚陵抚了抚觅秀的背脊,宽慰她说:“都是小事,没关系的。”
觅秀一双秀丽的眸子瞪得浑圆,看向她:“姑娘,这叫什么事,这怎么能是小事?奶奶的,要不是我一个人实在是打不过她们,我……”
话音至此戛然,觅秀立即站直了惊呆了似的看着自家姑娘:“怎、怎么能教姑娘给奴婢沏茶,奴婢……”
稚陵可从未计较过这些,毕竟她也从来不够格当什么正经的主子。她打岔道:“究竟发生了什么?”
觅秀瘪瘪嘴:“那些个人当真是仗势欺人。姑娘不也是杨郡薄氏的表姑娘么,姑娘出了彩,那杨郡薄氏难道还会少了风光么?”
稚陵心中却似被鼓槌重重一敲,竟然和杨郡薄氏沾了边?
她急于知道下文,所以看见觅秀因为骂人骂了半箩筐而舔了舔嘴唇时,她立即又给她倒了杯冷茶,弄得觅秀脸上更红了,直摆手:“姑娘快折煞奴婢了。”
觅秀虽是个炮仗性子,泼辣有余端庄不足,但待她一直顶好,稚陵可从不觉得给她倒一杯茶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稚陵笑了笑,叹说:“我可是急着知道你探来的情报呢,你这丫头偏还吊我胃口。”
觅秀这才长长地叹了口气,十八岁的年纪倒似八十岁的老翁,惹得一边的寻音笑出声来。
“姑娘,奴婢去了内务监打听,那领事的大太监简直欺人太甚,昨夜里姑娘分明也是他做主迎了进来,今日竟然翻脸不认人了,说,说献舞的姑娘分明是杨郡薄氏嫡支的大小姐薄云钿,哪里来的什么表姑娘裴稚陵?——可真真是气煞人也!”
喔,太可恶了。
稚陵心里淡淡地闪过这句话以后,竟然了无波澜。
她觉得自己这般懒怠去应付的状态不好,打起精神来又想了想,喔,简直是太可恶了吧。
随之觉得有种奇妙的解脱感。
她倒是有个大胆的想法,既然贵人自家的侄女儿要去出这个风头,她作甚要去找死呢?
但这个想法它之所以是个大胆的想法,乃是因为若她真的按照这想法想下去,怕是今冬的令蓝花解药就没戏了——那才叫真的找死。
她缓缓落座,一面揉着自己发疼的小腹,一面被迫着去想想对策。薄家嫡支的大小姐,那是太后的亲亲侄女儿,太后大约舍不得她受一点儿委屈吧?
但她跟国君即墨浔又八竿子打不着,除了今日的献舞,哪里有法子去攀上高枝?
坊间传闻里,即墨浔是一位清心寡欲的君主,据绛都街头花边小报上说,曾有媲美褒姒的宫女自荐枕席,晋君即墨浔对她谆谆教诲,教诲得那宫女泣涕涟涟,表示以后永不再犯。
至于教诲的方式么,私下里他们说是叫她一月里抄了八万遍《论语》。
稚陵想一想这八万遍《论语》就胆寒,摇了摇头,想着自荐枕席真是下下之策,万不得已也万不能选这路子。
她托着腮想了半天,终于磨磨蹭蹭地想起自己怕是只能去寻贵人了。
贵人正是这当今的薄太后。
她对贵人一向是又恨又怕的,恨自然是恨她怎么能够叫自己服毒,从此自己就受她的驱使;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