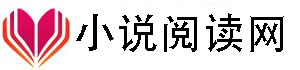22-30(6/36)
又咳嗽了两声。那堂倌压低声音,眉头却拧成个川字:“那位缪娘子可不好惹哩,她有人撑腰。”稚陵又想起来前几天听来的零零散散的传言,说那妇人是哪位大人物的外室——但确实是她这次差点误伤了对方,对方占理,她便说:“既是我的错,不管她有没有人撑腰,总得赔她才对。”
他的剑益发萧瑟冷厉,从前还有许多花里胡哨的招式,看起来格外晃眼,现在通通都没有了。
堂中仅剩下了她和观主两人,观主才缓缓地开口:“薛姑娘的来意……贫道大约猜得到。”
稚陵不由得眼前一亮:“那,道长,有办法么……”
桐山观主捋了捋胡子,慈蔼目光落在她跟前,微微一笑,说:“有。只是要花费些时间。”
稚陵说:“是配药!?”送不出去了。
昏烛摇晃,终于开口,嗓音沙哑:“不用追了。”
红烛烧到了尽头,噼啪爆了一下,彻底熄灭。
稚陵被声音惊到,抬起眼睛,朦朦胧胧中,船行江里的水浪声清晰入耳,她揉了揉眼睛,自言自语:“怎么又睡着了。”
她近来格外困倦。
客船摇晃着,她望了一眼,似乎长夜将尽,心头意外一刺,不知怎么回事。她借着窗外微光看向了床榻上躺着的男人,钟宴伤了好几处,那些杀手的暗器上似乎淬了毒,不过太医说不严重,只是解毒要多费一些心思,他们云云一堆,她似懂非懂。
除了“细心调理”这四字,她却听得明明白白。
这一回他们好不容易可以走了,况且……走了这么多天,不曾遇到追兵,即墨浔要么是自顾不暇,要么是放弃追过来——无论是哪个原因,既然远走,旧事也不必再提了。
钟宴自然要回西南镇守,否则西南周边那些小国,指不定要兴风作浪,那可不好。
但钟宴也跟她说过,他打算辞了官——即墨浔准不准,他都要辞,届时与她去家乡隐居。若是她爹爹愿意,致仕以后,也可一并来,一家子团团圆圆的。
钟宴的原话是:“我原本就是因你才决心离开宜陵,答应父亲,建功立业。如今,你我的心愿已成,荣华富贵,只是过眼云烟。”
她问他:“我的心愿,我知道。你的心愿是什么?”
他咳了一声,目光轻柔地望着她:“是你。”
沿运河南下,取道宜陵,去故乡看一看,再到西南去。
观主点了点头,稚陵疑惑起来:“难道不是什么‘姻缘’……什么‘因果’么?道长从前跟家父家母说的……”
观主笑着摇了摇头,说:“世事变幻莫测,从前是从前,今日,是今日。”
稚陵暗自嘟囔,早知道就早一点来了——也不至于四处相亲,碰到好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。
她自是满心感激,便又问道:“那,配的什么药,大概要多久?不知麻不麻烦,若是麻烦,烦请道长给一张方子,我请爹爹帮忙。”
观主闻言,笑说:“姑娘不必担心,算不上麻烦,只是耗费几日时间。这几日,姑娘可安心在观中住下,贫道进山采药,三四日可归。”
“只要三四日?”
稚陵喜出望外,不由抬手抚了抚胸口,差点高兴得晕过去。
观主他允诺此事,现在他得了闲暇,立即换了装束,动身出发了。
这叫稚陵心里佩服,九十六岁的老人,尚有如此说走就走的魄力。
她回头将这好消息正要告诉钟宴,他等在回廊底下,她刚张嘴,就看到钟宴身后,鬼一样出现的白衣男人,幽静地望着她。